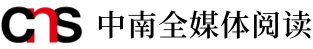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多令编辑:杨雁霞2023-12-11 17:26:08
到完成《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时候,胡安焉已经换了十九份工作,这些工作无一例外是枯燥的,当物流公司的打包员、倒包员、补码,送快递,做保安……这些工作的枯燥和艰难甚至让这本书无法做套色处理,长期的倒班,让他在一个阴晴如一,四季消亡的世界活到了44岁。
按照福柯的理论,他就是一个活在公司“规训”里的人,久而久之,即使公司不规训他,他也很自觉地规训自己,按照经济法则做好那种很机械的劳动,每派一个件有0.5元,每揽收一个件有1.6元,如果想在北京达到270元日薪,就得这样去生活:“我吃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10分钟等餐,10分钟用餐。因为我每分钟值0.5元,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考虑到中国有数千万人在和他一样从事这种司空见惯的职业,对于这种职业书写,大众通常会缺乏像对宇航员运动员那样的好奇心——那么是否值得一写,是否值得出版,就成为了一个拷问,就像加缪拷问西西弗的劳动是否荒诞一样非常严厉:一种极度缺乏美学和旨趣的生活,从来也不会有《西线无战事》里保罗式的悖逆或者堂吉诃德式的浪漫发生,甚至连做一个灵魂上的局外人也是在浪费时间。大家都是日复一日蜷缩在人生的壕沟里,怜悯自身手足的溃烂,偶尔的光明和幻想总是转瞬即逝。
既然无趣至此,又非写不可,那么哪怕是一个机器的世界,也得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吧?但事情往往又不是那么简单。他自称并非一个爱抱怨的人,但和同行同事在一起,不抱怨似乎就没有什么可聊的,大家都在抢好送的区域,谁抢到好的,别人就只有不好的,不可能大家都好,新人只能从最烂的小区送起。这样的零和博弈真令人沮丧。
尽管胡安焉很爱读书,读乔伊斯、菲兹杰拉德和伍尔夫,也尝试写作,但这并不能成为工作的解药,因为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前,他在这些事情上最多只挣到过几十块钱。这彻底背离了读者的思维惯性,理想不但没有指引生活,反倒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背叛。普通劳动的慰籍,通常只会来自于普通的事物,绝难等到什么天道酬勤奇迹降临。读这些让人灵魂出窍的书籍,他得到的最大感悟乃是伍尔夫所写的利蒂西亚女士,她一生吃尽了苦头,却在濒死之际“喜欢她的鸭子和枕边的昆虫。”
他断言这是“一种伟大的失意”,得出结论是“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那么如何做到不怀怨恨,如何过下去,就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书写。当你无法选择如何活下去的时候,你至少还能选择活下去的态度,谈谈你的看法。
比如他立志向两个客户复仇,认真记下了他们的地址电话。这两个人都是具有“上帝思维”的人,明明是自己填错了地址,还让胡安焉自己出转递的那八块钱,因为他们是“上帝”嘛。这不是八块钱的事,而是让这一份职业蒙羞,胡安焉最后得到的宽慰,乃不是复仇成功,而是自己竟然能够放弃复仇的念头。
从事这样一份职业,很难有为了高尚光辉去赴汤蹈火的机会,那么,尽量去记住尊重和友善,就不失为一种可靠的自愈方式。有一个中年男人,为了给他开门费了很大的劲,只是为了和他当面说声谢谢,其实他完全可以让胡安焉把快递扔在门口离开的。还有一个大爷,因为沟通不畅整整等了他三个小时,最后只是假装生气而已,还俏皮地告诉他:之所以不让他送到家里,是因为买的这玩意不想让老婆知道。这种不抱怨的客户,让他羞惭于自己的抱怨。在品骏快递解散的时候,一个客户表扬他是最认真负责的那个快递员,这几乎让胡安焉飘了:我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宽慰和灾难也会交替发生。他的快递生涯最大的灾难乃是生病半月无法出工和赔了客户一千块钱,这两件事都让他很痛苦。按照培根的说法,无论工作的枯燥和艰难有多大的罪孽深重,那都远远称不上是痛苦,因为真正的痛苦只能是肉体上的,如果肉体不痛还感觉痛苦,那唯一的根源就是“想多了”,既然胡安焉的病毒性肺炎好了,脱落的指甲又长出来了,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无病呻吟——这就是经济学工具论之类最混账的地方,甚至在经济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胡安焉们所向往的稳定富足,往往会仅仅因为一场疾病,一点意外就迅速坍塌下去。大多数人的财富自由都是徒劳,他换的十九个工作几乎都是平行的,从无向上的能耐,身份转来转去,顶多也就是个小时工和正式工的区分。
多余的烦恼并非由于多余的欲望而产生,而来源于有过切肤之痛的生活危机,所以他写下的宽慰和痛苦尽管司空见惯,却是一个劳动者所能做到最真诚的。
所以我们能从阅读里找到一条非常不显眼的叙事脉络,一种弱得不能再弱的“弱情节”,一点点关联上自身的委屈、麻木,还有收工时的二两白酒和一个突然释放善意的上司。他并不是天生具有慈悲心肠和乐观主义态度的快递员,他开始是带着抱怨去忍耐,后面设法尽量不去抱怨——如果说这是人生修行都是在夸大其词,实质上是人人都有打磨生活粗粝的本能。
他也许做得比别人略好一些,除了脾气略好一些之外。因为他有过一些阅读和写作的经验。所以比其他快递员更容易思考这些,将善和释然的提炼为了日常生活的要义。这正好应验着康德所说“个体向善的能力”,他具有很自然的这种禀赋,很自然地就将它捡拾起来,有的人却要经历很残酷的转化才行。
对于胡安焉这类人来说,这种禀赋并不指望额外的奖赏,当然也最好不要遭什么报应——对他理想的回应,是不必有热烈的掌声,因为这实在太平凡了,不能因为有人很认真地写了这些就去激动,胡安焉最近因为过多的采访也非常厌倦。但必然有很多也很普通的阅读,这不仅仅是他处境普遍性的使然,也是在稀释着各种被夸大其词的人生,也能减少幸福指数中的物质比重。
胡安焉因为这本书改变了生活,它卖得很好,他已经为此定好了以后的写作与出版规划。但所有立志于写作的人都不必去嫉妒他,写如此平凡的东西也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不谈运气似乎很说不过去,但文学就是这样,由于写作所带来的不平等,反而是这个世界最值得尊重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