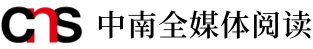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韩浩月编辑:杨雁霞2025-07-11 10:31:36

《万物有信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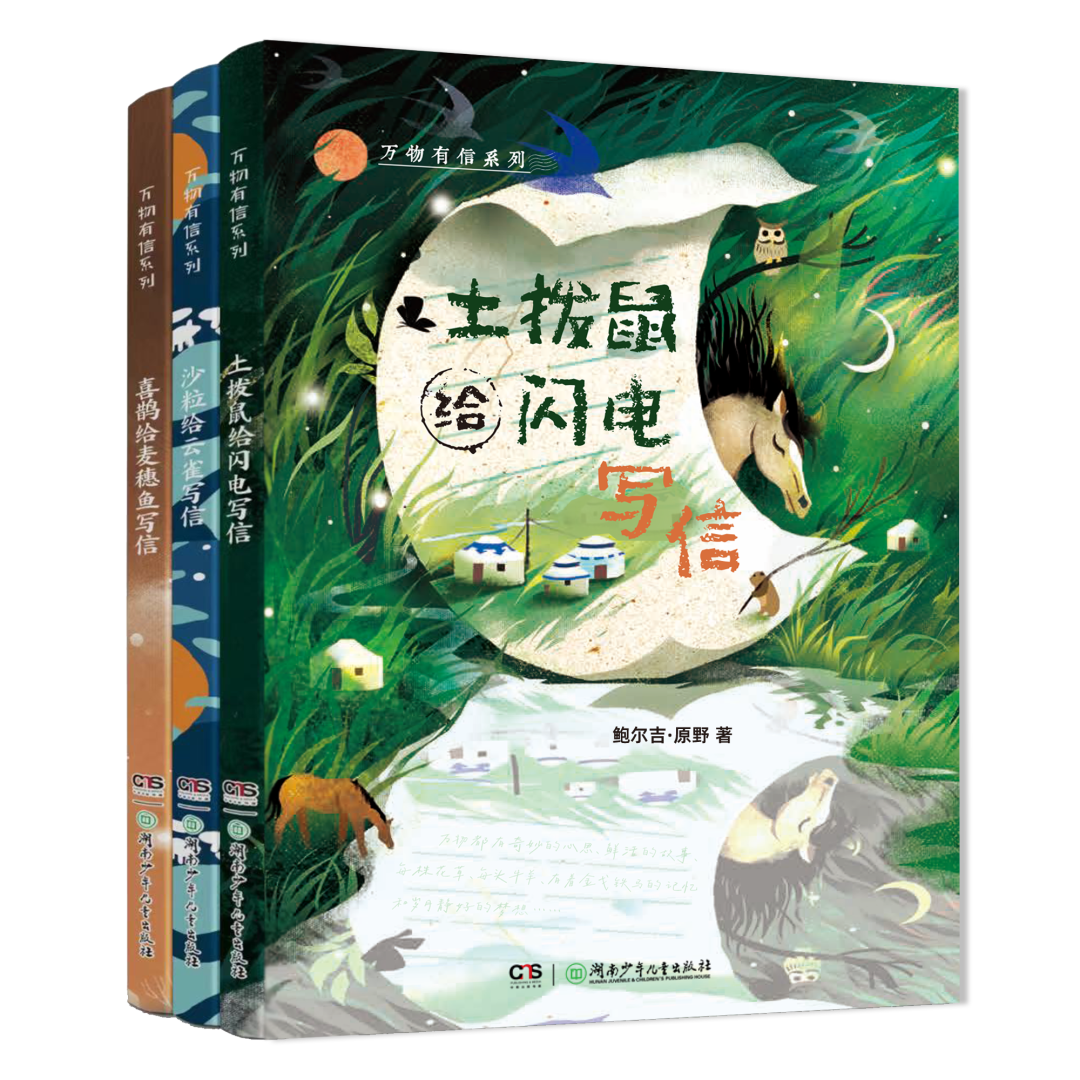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 / 著
定价:114.60元/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5年5月
鲍尔吉·原野的“万物有信”系列,刊发于《当代》《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最近结集为《万物有信书系》出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全套书共收录170多封书信,分为三本:《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喜鹊给麦穗鱼写信》。
《万物有信书系》并非专为少年儿童读者而写,尽管书中充满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一颗赤诚的童心,完全符合这一群体的阅读口味,但成年读者哪怕只读完其中一个章节,也会感受到作者的写作出发点和内容价值指向,都超出了“提升少年读者阅读欣赏水平”这一基本定位。它是在认可“万物互联”“万物智联”时代已经到来的前提下,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同步于当下的主动做法。阅读这些文字,会觉得只要人们还拥有敏锐、快乐、激动的能力,那么,即便未来的生活被机械与智能包围,也依然可以体会到“生而为人”的那份独特与不可代替性。
鲍尔吉·原野的每本书中都有一处美丽的草原,《万物有信书系》也频频写到一个名字叫万度苏草原的北方牧区,那些纷纷“提起笔来”写信的喜鹊、麦穗鱼、羊羔、白乌鸦等都居住于此。书信对草原万物有大量的描写,但当这些描写转由万物本身叙述出来时,便带来了一种神奇、清新、别致的阅读感受——它们在天上地下、云中河里所看见与发现的,与人类视角竟有如此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借由书信体的方式被送进读者的视野,读者便化身为收信人,与“写信者”无形中建立了一种亲昵的关系。这种无处不在的亲昵感,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
会写信的还有沙粒、马头琴、灰尘、马镫、铁皮水壶、风滚草、水盆等,如果小动物说话在童话写作中常见,那么,如此大批量的用具、物品、有机物质与无机物质等,都纷纷具备了人的视线、感情、思想,便瞬间打开了作品的书写格局。作者由此建立了一个立体、宏大同时又平等、公正的宇宙观。人类中心论被淡然地放在一边,一粒沙、一棵草都具备了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与权利。而这一格局的形成,恰恰在于书中万物掌握了语言、文字、情感之间的奥秘。作者没有打算充当它们的事务代言人,而是成为其中一员,是倾听者,是书信代写者,除非对世界、宇宙不再怀有丝毫浪漫想象与理想期待,否则很难不被代入其中。
170多封书信分别交叉进行,写信者与复信者的组合新奇到匪夷所思,比如蜥蜴给冰雹写信,螳螂给辣椒写信,蚂蚱给灰毛驴写信……这构成了一次网状、球形的跨界对话。它们分别打破了自己活动区域的界限,以及它们对自身认知、外界评价的桎梏,通过一封封书信,完成了一次颇具震撼感的“情感外交”。它们的书信里充满好奇、憧憬、试探、祝福等,这些人类的情感底色构成在淡化、粗糙化、钝感化之后,需要有这样的“万物通信”进行一次细致的打磨。如果经过这样的打磨之后,人的情感能够回归到友好、纯真、热情的本真状态,那么,这些万物之间的通信也便完成了它们的任务。
在170多封书信中,没有一封是同类写给同类的。一只喜鹊写给另外一只喜鹊的信会是什么样?一条麦穗鱼眼中的河流与另外一条麦穗鱼活动的区域有何不同?可以想见的是,同类之间相处久了,难免会出现固化的视角与观念,难免会因为重复与琐碎而有流俗的倾向。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鲍尔吉·原野将人类学研究中的“关怀他者”引用到了《万物有信书系》的写作中。在人的生存愈加被局限于手机、社交媒体与个体空间时,对于遥远事物与陌生领域的探索与追寻,也开始从人的属性中淡化,“关怀他者”是“世界大同”必不可少的支撑,而在《万物有信书系》中,每每看到鼹鼠写给蒙古百灵的信、看到松鼠写给萤火虫的信时,总会油然而生一种“关怀他者”所带来的与胸怀有关的开阔感。
每一封信,都得到了回信——无一例外。
写信所释放的信息,在复信中都一一得到了回应,这是《万物有信书系》的写作结构和创意核心,但无形中也迎合了人们对于渴望互动、彼此理解与安慰的内心需求。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争取被看见的时代,能够看见别人是一种能力。书里使用了包含称谓、落款、昵称等在内的书信格式,但在格式之内,那些流动的情绪如同草原上的河流,时而从壮丽山川落下,时而静缓流过茂密森林,时而在广袤草原奏响和鸣曲。每一封得到回信的书信,都在走向富有意趣与希望的未来。
在鲍尔吉·原野看来,写作这套书系并非“生活积累的较量”。与作者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万物有信书系》对素材的使用是简约、克制的,“万物写信”的形式解放了作者的语言与内容。每通书信,打开的都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新世界。作者畅快地撷取,使得书里充满闪现的灵光,因而读者阅读这些文字,会由衷地感到快乐。文学的快乐属性,在此书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挥,而读者读完之后所获得的平静与启迪,则彰显着文学在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力量感。